限制視角:客觀的不可靠敘事
徐冰曾經設計過一個藝術作品,名為【蜻蜓之眼】,整個作品是透過無數個網絡攝影機下記錄的畫面進行拼貼剪輯,然後透過這些監控畫面的奇異組合,竟戲仿出一個人生波瀾的故事。而電影的成片,很難說不是更多個更大型的網絡攝影機下被記錄的諸多碎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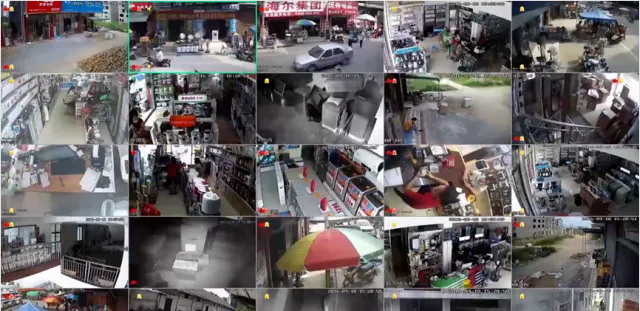
在【斷·橋】中,最能給人真實質感的記錄畫面,正是看似那些高度失真的網絡攝影機視角下的諸多眼睛。故事一開始,就是看似日常且庸碌的生活場景,不過不是以人的眼睛去看到的,而是出現了各種畫質粗糲的監控畫面,這些畫面以各自的不可靠敘事,從只在自己的角度完成了黃雀市過江大橋那驟然垮掉的一瞬間。
然後故事才進入到沒有網絡攝影機出現強烈主體性的電影敘事。當然整個電影視效過程,還是穿插了大量的網絡攝影機所拍攝的畫面。這過程裏,既有來找警察的監控錄像的調取和分析(包括各種照片資訊),也有來自可視門鈴的畫面,當然還有各種互相偷拍的照片或記錄。
最重要的證據,則是完全站在菊 懷義的第一人稱視角下的偷拍記錄,這份偷拍記錄成為整個事件最重要的證據。而在他的偷拍鏡頭下,他自己沒有出鏡(這是當然的)。可是我們進一步去思考時,會發現一個更加隱秘的設定,鞠懷義的正臉曾經以特寫鏡頭出現過嗎?答案是沒有。
當他墜樓成屍時,整個面部已經被軀體掩蓋,看不清模樣。也就是說,站在映像美學的角度來看,因為他從未入鏡,所以我們不得不懷疑菊懷義作為人的本質存在性。或許他的名字諧音就在暗示觀眾,看似客觀的視角其實是一個不可靠敘事:去懷疑。
在維爾托夫的蒙太奇理論中,將其稱為第四人稱單數。
「在維托夫那兒,運動區間就是感知、驚鴻一瞥,也就是眼睛,然而在此僅指涉著非肉眼的絕對固定的眼睛」。這種攝影機眼睛是物質之眼,是機器意識,並不是人的意識。在蒙太奇中,機器、人物、結構、場景、建築等等都是不重要的,一切生命都在事件之中,而事件是由蒙太奇建立的,或者說事件本身受制於機器的「運轉、跳越、震顫、閃光」。事實上,維爾托夫並沒有將生命看作是機器,但他將機器看作是有「生命力」的,他「在現實中所發現的是分子性小孩、分子性女人,也就是物性的小孩和女人,如同被謂為機制或機器的系統」,可見,第四人稱單數是有「生命力」的機器之眼,是機器意識體現,是人的「第三只眼睛」。其實在電影的名稱裏,就以非常明顯的斷點告訴了觀眾,那就是「斷」與「橋」中間的「點」。對於對大部份電影來說,名稱中不會出現標點符號。出現符號的一個現實考量,就是與其他某部已有名氣的作品相區別。但是選用何種符號,所起到的語言潛層效果就會出現較為明顯的差異。
【斷·橋】中間的點,具備了多重可解讀的空間,他們相互疊合在一起,將整個故事封閉在黃雀市這一陰雨綿延且無法逃脫的空間中。
首先,這個點是蜷縮在整個斷橋中的,隨著這個詞語(大橋)被折斷,他隨之被破土而出。他既是斷點,也是整座大橋的設計師,聞曉雨的父親聞亮。一開始斷橋事故成為推動故事劇情的核心驅動力,而隨著電影進入後半段,斷橋中的點,也就是父親被害的真相逐漸變成前景,斷橋本身則變為與整個逼仄荒蕪的廢墟背景的一部份。
然後,如果將斷橋從橫向變成縱向,那麽這個點從頂部看去,就是影片一開始看似毫無存在感的一直亟待爆破的井塔。但所有腌臜的過往都在周遭空間中:不管是堆積成山的人民幣,還是用來毀車的炸藥,以及墜樓而亡的菊懷義。而最後的爆破,將整座井塔夷為平地,孟超與朱方正也都掩埋其中,不得自拔。這正與電影一開始斷橋崩壞並從中發現「點」的敘事空間形成一個閉環呼應,讓整個黃雀市的時空故事變成一個無法從內部突破的壓抑的氛圍場,
而第三個斷點,則是一開始所說的,不斷從俯視的第四人稱單數去冷冰冰觀看這個世界的,網絡攝影機。值得註意的是,如果我們將斷點看作是網絡攝影機,則形成一種視覺成像空間的嚴重曲面。網絡攝影機斷點在電影裏的功用是用來觀看斷橋的,但電影名稱裏的斷點,卻是用來指向觀影者的。於是「他看到了自己的被看,凝視著自己的被凝視」,形成一種縫合的真實空間。

詳見下表(不和正文完全匹配):
| 【斷·橋】中的 · | 實體的點 | 掩埋的點 | 凝視的點 |
|---|---|---|---|
| 作品裏的人物 | 蜷縮的聞亮 | 崩壞的朱方正 | 攝影的菊懷義 |
| 背後的隱喻 | 真相-過去-揭開(尋父) | 包裹-性情-本性(惡) | 網絡攝影機-凝視-限制視角 |
語言質感:微觀權力的滲透
為了突出這一空間的異質性,電影中交替出現了兩種語言表達系統,那就是普通話與方言的對抗,以及從中產生出的川普話語。在電影中,黃雀市屬於巴蜀地區,裏面大部份人說話都是用極具濃郁特色的巴蜀方言進行。在這樣一個以地方區域性表達切割空間的電影裏,方言變成常態,普通話則變成了非常態,這種非常態,成為一種福柯所說的微觀權力的滲透性。其中典型代表人物,就是朱方正。
朱方正在整個電影中,都以普通話與其他人對話。而且在對話過程中他反復強調要下屬說普通話,似乎只有說普通話才能形成與他的對話空間。同時,在說話時還不忘援引曾國藩的名言,援引的時候刻意減慢說話的節奏速度,形成一種不怒自威的感覺。
這種感覺即便是在井塔中,將聞曉雨拷在一旁與她對話時,依然保持著非常文縐的感覺:一邊是聞曉雨歇斯底裏的咆哮,另一邊是朱方正一句一個刻定的評價「潑婦」。我們當然可以將朱方正當做一個雙面虎的角色來看待,但是他的話語表達的過程是一種非常官化的權力規訓過程。如果不是鞠懷義的偷拍攝像,僅僅看到朱方正的言行,我們就會得到一個更加簡單樸素的結論,這個結論會與聞曉雨對其的認知高度重疊。
朱方正是一個壞人嗎?至少從電影的第一幕家屬向他下跪,他說一定要承諾將整個事件給予一個合理的解釋來看,不像一個壞人。他收養聞曉雨的目的是什麽呢?我想應該是為了贖罪。而這種贖罪的良善的本性,很快被他自己所在的官位上的已經成為一種規訓系統的表述方式所碾壓。這樣他才可以一直心安理得的一邊隱瞞聞曉雨父親的死訊,一邊把自己當做親生父親一樣的去對待聞曉雨。
而且他還借助了很多別的手段來表達自己的良善性,雖然看起來很荒謬。我們在電影中能看到兩個關鍵性的場景,一個是他將大捆的人民幣放在一個無人進去的爛尾樓中,並且為這些人民幣不斷的上熏香。另一個則是,他會時不時的開啟梳妝台,然後點上艾草敲擊法螺為自己誦經。當他自我合理化之後,就變成了一種以普通話為基礎的言語表達形式,將一個非常復雜多面且狡邪的形象變得極其具有柔性。
演員範偉則透過非常多的微表情以及諸多肢體小動作將這個人物刻畫出來。其關鍵點就在於,他能夠非常擅長說服自己,並透過合理的諸多鏡頭語言,然後將說服後自己很快消化掉。
反過來說,在整部電影中大量以四川方言表達的內容, 更像是揭示出一種與這種政治話語體系完全割裂的底層生活空間 。馬思純和王俊凱在交流的過程中,一開始會用普通話相互試探,直到她們彼此熟悉之後就改為使用巴蜀方言。 這意味著他們放棄向上尋找解決問題的話語路徑,而是改為向下深入到底層空間中去探索真相,這種探索的過程是一種對於頂層話語的不信任,它同時也是對頂層話語背後的攝像監控畫面的抗拒 。
於是我們會看到在他們尋找真相的過程中,大量的都是經由與其他人在交流的過程中一步一步拼湊出事件的真相。於是在第一部份所說的那些由監控網絡攝影機所形成的拼貼的畫面,他們本來是可以還原世界真相的,但是在這個話語系統中它們失效了。
我們還可以發現那些監控網絡攝影機所呈現的是沒有語言表達的畫面,而這些方言的對話則是呈現的過去的記憶交流對話與情感,他們沒有畫面。
來自於底層的鄉土空間和方言的交流,給了聞曉雨以更強大的生存力量。使得她貢獻出了在我認為整部電影裏非常精彩的兩個名場景。
第一個就是她在與孟超爭執的過程中驟然吻上了對方。他們都爭相想要保全對方的生存,也都想要自己先出面去解決問題,於是經過了極其激烈的爭奪之後兩人擁抱在一起,這是一種極其具有山城特質的戀愛方式,讓人感受到一種強烈的原始野性力量。反觀說普通話的這些成年人,我們會看到當事件可能敗露之時,他們是在想方設法先保全自己,所以這時候具有官話特色的普通話對話,反而成為了一種相互傾軋的狀況。
第二個則是她回到家裏給朱方正過生日的場景。在這個場景下我們會看到,這時候的聞曉雨已經完全不說普通話了,她操著一口非常柔和且具有力量感的方言腔和朱方正對話。而朱方正則是采用普通話,不斷的強調自己的贖罪心態,兩相比較之下,我們就能看到兩種不同的語言質感的強烈對抗。

擬親關系:少年們的抱團自救
在整個極具壓抑特質的陰雨連綿場景下,少有出現的溫馨場景則是在孟超的爛尾樓房間中所形成的三人式的擬親小家庭。孟超、聞曉雨和藍莓,每個人都經歷過喪親之痛,無論是姐姐父親還是母親,都指向成年人這一概念,同時也失去了成年人社會的全部功能所指。
他們三人在這個小房間裏的嬉戲打鬧,一起吃紙包魚借由墻面上那盞忽明忽暗的鵝黃色燈光籠罩下形成的短暫烏托邦,更加反襯出一種以樂景寫哀的悲愴感。
這種少男少女之間借由喪失了對於親族關系從而形成的身份性的共鳴,支撐與扶持的方式也就取代了原有的他們所描述的成年人的家族構造的具體生活方式。家庭關系是缺位的,就如同斷橋是破碎的,維系這斷與橋之間中間的那個點,並不是銜接人與人之間的血緣關系,而是由於一種單純的相似性所形成的擬親關系。
這種關系不能不說是在更加社會心理學層面上的抗拒社會化與抗拒成長。作品所描述的時間是2011年前後剛成年的少男少女們的心理生存狀態,他們正好契合了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非常典型的一種社會癥候群,那就是被原生家庭壓迫的逃避,它們逃離家庭,並且渴望形成自我獨立的個人意識,不過這部電影並不是透過一種更加正向反饋的方式所呈現出來的,而是透過一種更加逼仄的個人生存境遇,甚至可以說是決斷主義的方式所表現的。過程中自我意識和強烈的情感需要,並沒有在作品中被呈現,他們是洶湧澎湃的,卻是在平日的交往中被克制的。
如果我們將整個黃雀市看作是一個人的大型精神生活空間,那麽斷掉的橋和死去的長輩角色,在意象上就是相互襯托的。短暫的逃離之後,在哪裏可以獲得一種新的認同感呢?
孟超給了我們一個看起來非常荒誕不經的選擇,那就是進入【世外桃源】。 而這世外桃源是由那些老年人所跳舞的歌廳,晦暗的燈光交錯,以及將自己從具象的實體變成吼撕的聲音,才能得到的 。
當然這樣的烏托邦也是不現實的,不能長久存留的。就像斷橋在電影的結尾也沒有被重新搭建起來,它成為了一道懷舊的景觀。甚至我們可以用博伊姆的話來說,這是一種反思型的懷舊,它並不是註重要將其修復成未曾損壞的模樣,而是要保留被破壞的瞬間,形成一種強烈的反思特質。斷橋裂開了,而斷橋中間的點卻張揚著,形成一股新的力量,將那些一直將它壓抑的、讓他規訓的、使它異化的推翻之後,形成一種肆意張揚的野望。










